遇见|这届创作者太难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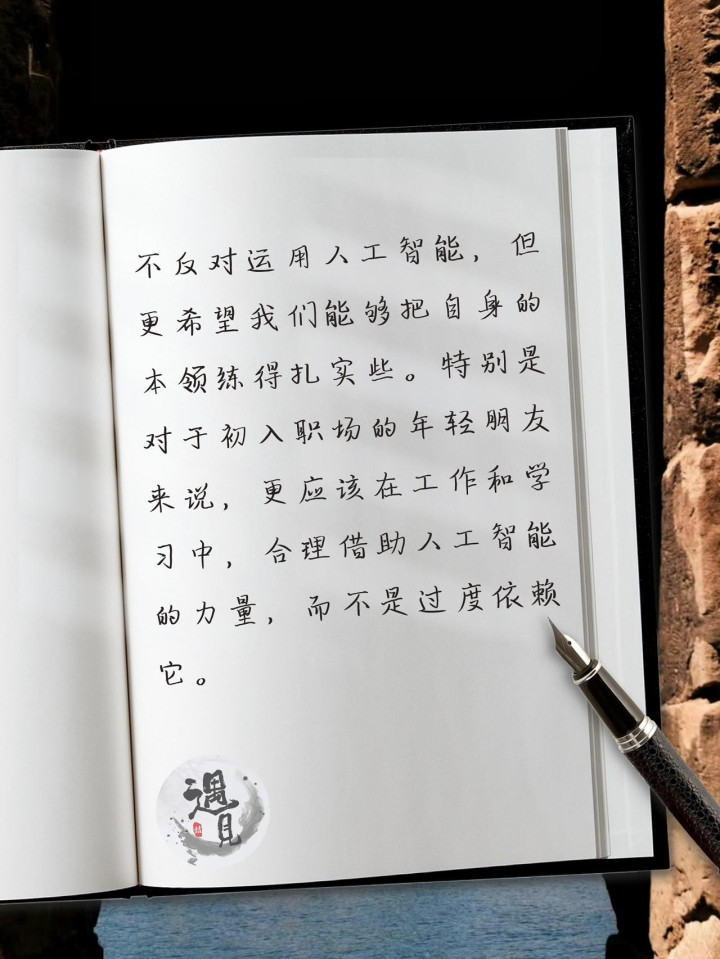
清晨的电梯间,几位媒体同行的对话像面镜子,映照出这个时代的创作困境。“现在朋友圈发原创设计,总有人问是不是AI画的?”资深后期林姐的感慨像投入湖心的石子,激起一圈圈涟漪。在这个全民AI的时代,创作者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——那些浸润着体温的作品,该如何自证“人类基因”?
实习编辑小冉突然掏出手机,屏幕上赫然是她的“血泪史”:两万三千字的毕业论文被检测系统标成调色盘,满屏红黄预警如同交通信号灯。这个倔强的姑娘至今说起仍眼眶泛红:“每个标点都是深夜的见证,从开题到终稿改了11遍,现在却要证明自己是人类作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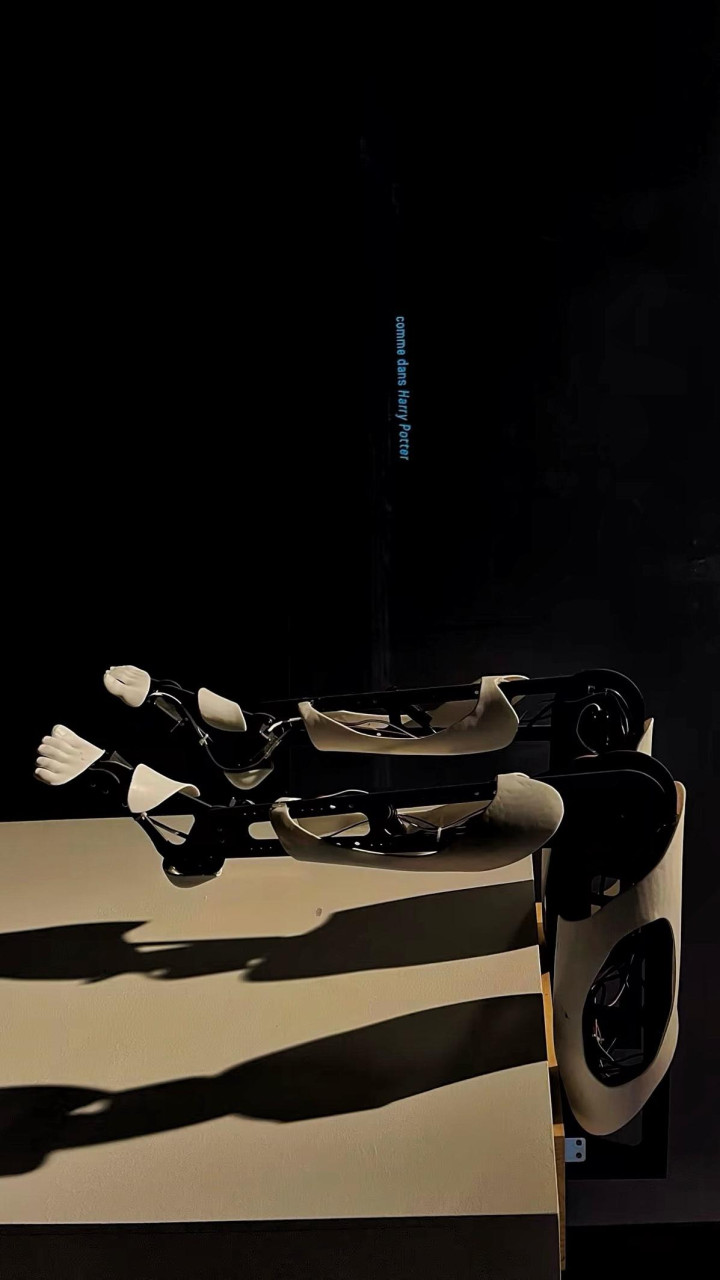
更有趣的是,现在连人工改稿都逃不过AI检测。我表弟在实验室发现,他们组把原创论文用ChatGPT润色后再人工修改,结果AI浓度反而飙升。他说:“这就好比用测谎仪检测真心话,测着测着把真话都筛没了,还挺无奈的。”
后来,小冉靠“自残式写作”勉强过关:故意写病句,留错别字,把专业术语换成大白话。当她捧着面目全非的终稿时,凌晨四点的星光突然变得刺眼。“降AI率成功的喜悦没持续几分钟,就开始觉得失落。”那些被删改得支离破碎的文字,像被拔掉羽毛的候鸟,再难飞向理想的天空。

听着小冉的故事,我的思绪不禁穿越到了2007年,我的中学时光。那时,在班主任的鼓励下,我怀揣着成为一名专业码字工的梦想,热衷于参加各种征文比赛。每周揣着稿纸坐27路公交车去延安西路的少年时代报社,只为听编辑老师说句“这段描写有灵气”。2010年在黔灵山征文赛,当我的《林城絮语》与叶辛老师的《黔灵山记》同台领奖时,钢笔尖戳破稿纸的震颤,至今仍在指尖留有回响。这种真实的创作快感,是现在刷十个AI生成的金奖文案都比不上的。
说实话,我觉得写稿是一项特别烧脑费心的苦力活,如今的文字工作者正面临集体焦虑:AI分分钟能吐出十万字行业报告,通宵改稿的编辑开始怀疑人生。但真要AI走基层蹲半个月写拆迁纪实,它能闻到步梯楼里霉味混着煤气的味道吗?能体会婆婆摸着老墙砖时那句“这砖比我爷爷岁数都大”时的颤抖吗?这些带着体温的细节,构成了人类创作最坚固的护城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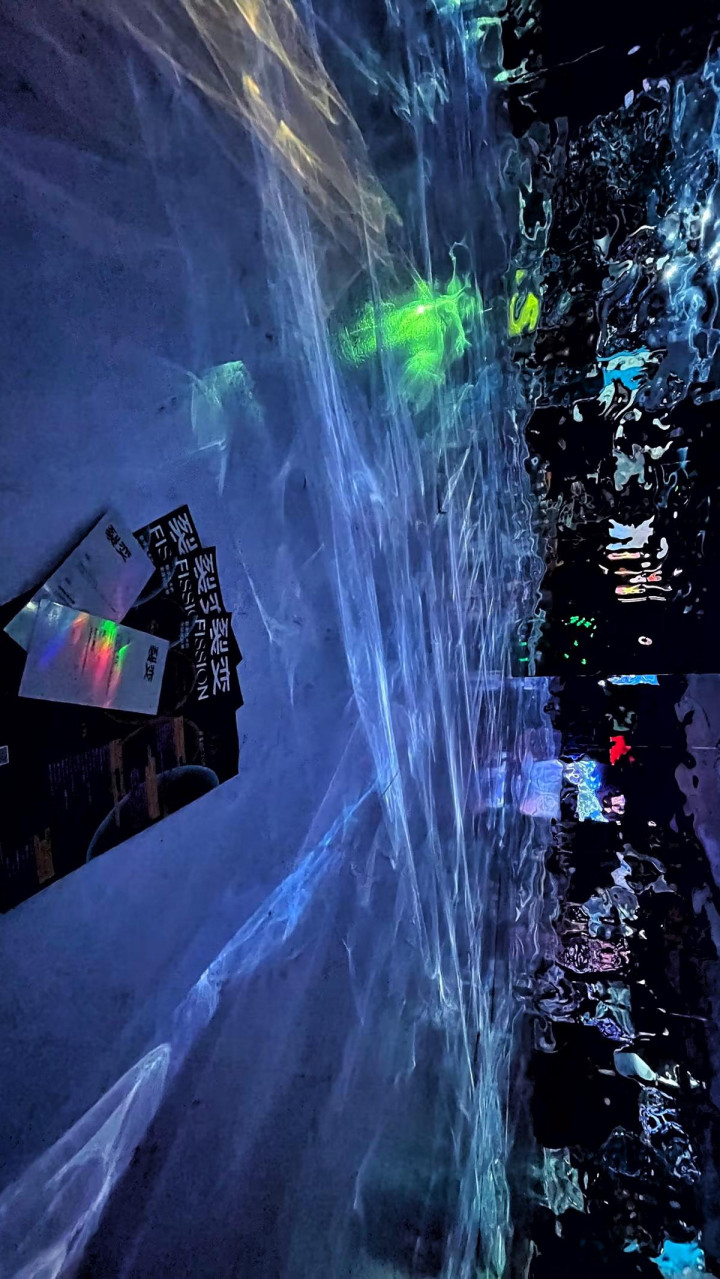
我家楼下开了三十年的面馆或许能说明问题:机器能复刻李叔的独家配方,却做不出他抻面时哼的那段陕北民歌的韵味。就像新闻里那个能写获奖微小说的AI,若让它体验失恋后写情书,生成的文字再华丽,也比不上深夜泪痕洇湿信纸的褶皱。
在这个智能时代,当AI能轻松生成标准答案时,那些不标准的真情流露反而成了最稀缺的珍宝。就像小冉修改论文时,虽然删掉了学术化的表达,却意外保留了某段采访的鲜活记忆——那是她在暴雨天蹚着积水,真真切切踩出来的文字。我一直觉得AI只是一个助手,它能帮助我们把表达变得更专业,逻辑变得更清晰,但核心内容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去创造。真正的创作从来不是填空题,而是要把自己的心跳声揉进文字里。

下次当有人说你的作品有“AI味儿”,或许可以笑着接受这份另类褒奖。真正的创作从来不是与机器竞速,而是在人机协作中,让算法为故事注入新的可能。毕竟,能通过AI检测的可以是代码,但能让读者心头一颤的,永远是文字里藏着的那颗人类心脏的跳动。
作者/摄影:王喆
